“一九七九年那是一個春天,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……” 而在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后,2017年的春天,中共中央、國務院印發通知,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。
眾所周知,“深圳速度”已成為代表改革開放的一座高峰;浦東新區依靠金融和高新技術產業聚集第三產業占比高達75%;和已經取得飛速發展的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相比,雄安新區“新”在哪,有何特殊之處,未來又將發揮怎樣的作用?
新一輪改革的突破口:從開放主導到改革主導
深圳是我國首個經濟特區,浦東新區則是我國首個國家級新區。雄安新區作為橫空出世的國家級新區,新華社給出的“千年大計、國家大事”八字標簽也佐證了其卓然的歷史地位。
深圳特區的設立,主要是為了吸引外資和擴大對外開放;浦東新區的設立則是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力度,并著力推進金融發展。雄安新區在改革開放中的角色盡管尚未明確,但從其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定位來看,有助于緩解政治資源與經濟資源的盤根交錯,降低尋租的空間,減少紛雜的利益集團帶來的改革阻力。從這個角度而言,雄安新區代表的是更為深層次的改革,也是難度相對更高的改革。這也與我國改革進入深水區的背景是一致的。同時,雄安新區還承擔著探索新型城鎮化及創新轉型的使命。
盤古智庫宏觀經濟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鄭聯盛認為,對比雄安新區和深圳特區、浦東新區以及其他國家級綜合示范區,雄安新區要承載“千年”的歷史責任,在經濟體制改革上發揮引領性可能是更加重要的。過去,深圳特區、浦東新區的發展更多是一種“開放”導向,大部分的改革是圍繞“開放”而進行的;而現在,雄安新區可能要承載“改革”導向的歷史責任,圍繞內部經濟發展新模式,進行更加深入的改革,“當然,改革與開放二者緊密關聯,但是,從開放主導到改革主導的探索,可能是雄安新區隱含的作用。”
資源稟賦:京津腹地提供強力支撐
在區位優勢上,深圳特區主要依賴于毗鄰香港的地理優勢,承接港臺等地的產業轉移和資本流入;而浦東新區則依賴于長三角的經濟腹地以及交通樞紐的地理優勢;雄安新區則主要憑借其臨近首都的地理優勢,主要依賴于政治資源的再分配。表現在資金來源上,深圳和浦東均更大程度上依賴于外資的流入,而雄安新區則主要依賴國內資金的再配置,吸收國內的富余儲蓄和產能。
對于規劃建設雄安新區的意義,發改委主任何立峰指出,一是重點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載地,可以有效緩解北京大城市病,與北京城市副中心形成北京新的兩翼;二是有利于加快補齊區域發展短板,提升河北經濟社會發展質量和水平,培育形成新的區域增長極,也可以與2022年北京冬奧會為契機推進張北地區建設共同形成河北新的兩翼;三是有利于調整優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間結構,加快構建京津冀世界級城市群。
未來的“京三角”:新增長極輻射冀魯乃至北方
目前,長三角和珠三角都市圈是國內經濟的兩大增長極。而作為國內三大都市圈之一的京津冀地區,整體發展極不均衡,北京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較弱。雄安新區的設立有助于實現區域資源的均衡配置,并發揮其自身的輻射帶動作用,真正將京津冀都市圈打造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三極。
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部副主任白明說,雄安新區和深圳特區、浦東新區重要性并列,但并不是照搬照套。“新區設立,有助于河北省集中承接首都功能,加強三個省、市之間的往來,并在全球范圍內吸引更優質的要素,”白明認為。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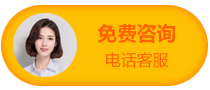
 京公網安備 11010502040384號
京公網安備 11010502040384號